硬核读书会
再看还是乐不可支。
(图/相声《电梯奇遇》)
对于春晚,人们到底还是有执念,因为它穿过了一个集体的时间——零点。有点像爱因斯坦所谓的,它可延伸、可具有文化意义,甚至可停留,从1983年起,一直被讨论、模仿、研究到了2024年。
✎作者 | 许峥
✎编辑 | 腾宇
一个事实是,“春晚”两个字从主流文化的代表,变得越来越像流行文化的暗号。
网友在谈论它的时候,动作非常灵活,有时超前,有时旁敲侧击,逐步产生百花齐放的效果。从《念诗之王赵本山》到《二进制小品》,不得不承认民间看艺术文化的目光是毒辣的,还有些批判性继承的味道。
一旦点进去,就很难走出来。
(图/《念诗之王赵本山》)
这些素材剥离于历年春晚,网友经年累月的二次创作,尽管粗糙,但绝对有力:“耗子都给猫当伴娘,齐德隆,齐东强,齐德隆的咚得隆咚锵。”微妙地组合起来,最终爆发成几百万甚至上亿点击的冲动与共鸣。
春晚诞生后的数十年间,社会早就变样了,但许多过去小品里的词儿,还能说到今天的点上。这种错位的幽默感叠加了时间的效应,从猴年跨到马月,回头再看,“你大爷还是你大爷”。

春晚,一年又一年。
(图/《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》)
春晚依然是特别的。它是一个覆盖了中国人年岁更替期间的大事件,网友屡次在二创视频中提及它、闪回它、重复利用它,大抵都有点为了触发记忆——当年,我们还听过这笑话呢。
说到底,春晚有个好底子,所以才防不胜防地为时代扣题。
01
春晚,民间幽默的
好土壤
语言节目的天职,就是对现实议题进行艺术发挥——把事儿说穿了,顺便把台下逗笑了。
赵本山的《牛大叔“提干”》,主题就是胡吃海喝。这么褒贬明了的一件事,搁在着急办事的农民身上,便促成了总经理的扯淡艺术:“人家拿那稿相当有派啊。往那一站就是:我说啊!就啊!我啊!都这玩意儿”,三言两语间,小品的目的瞬间水落石出,既好笑,又戳人脊梁骨。
一不小心整出了经典台词。
(图/小品《牛大叔“提干”》)
这是讽刺的好处,针对一个个议题,讲酒桌文化、讲形式主义、讲空巢问题、讲诈骗现象,从众多舞台手法中脱颖而出,它言之有物,而且聪明。
比如赵丽蓉讽刺奸商,揣着明白装糊涂:“还群英荟萃,我看就是萝卜开会”;牛群讽刺冗余的规章,对着话筒正儿八经:“副组长拿过来一看,先画了个圆圈儿,这叫圈阅,意思是基本同意”;范伟讽刺陪酒,上了台点头又哈腰:“他是上顿陪下顿陪,终于陪出了胃下垂”。
这酒怎么样,听我给你吹。
(图/小品《打工奇遇》)
在1987年反映男女问题的小品《产房门前》中,讽刺意味拉满。台上俩丈夫掰扯着产房里的事儿,“这个生孩子,那也是一波一波的,要说生男孩,那叮零咣啷都是男孩,要说生女孩,那稀里哗啦全是女孩”,谁也不是特别正面的人物,临了知道是女娃,两个人都崩溃。
演完了,郭达也不教育人,只是嬉皮笑脸地回一句:“这下我生了个男的,你生了个女的,咱俩可平衡咧。”点到为止。观众知道,编剧这是在骂那些说一套做一套的丈夫。
用“得了便宜还卖乖”的台词,切中时弊。
那是一个重男轻女问题
仍旧普遍存在的时代。
(图/小品《产房门前》)
写实也好,譬喻也罢,守着春晚笑完了,回过味来,觉得真章都在那几句插科打诨里,它观察了群众的困扰,就事论事,掐着秒表抖包袱,套上荒唐角色,演活了中国观众共同的内部梗。
几乎所有中文使用者,都能立刻意会啥是“俺叫魏淑芬”和“范乡长诞生了”,升职了那叫“产房传喜讯”,被谈话了那得翻出“母猪的产后护理”,前脚热点事件刚发生,后脚就追根溯源地评一句,“火车跑得快,全凭车头带”,这边厢喊一声“”,那边厢准能回上“一百八一杯”。
这叫圈阅。
(图/相声《小偷公司》)
广大群众借着掷地有声的包袱,洗牌、码牌、抓牌、看牌,从此幽默便有了具体的样子。
不管好赖事,都能拿它们活用,精准对应。批评家詹姆斯·威廉·凯瑞认为,“我们先是用符号创造了世界,然后又居住在我们创造的世界里”,翻译过来,这就是脍炙人口了。
一些二创甚至走向了更抽象的道路。的三弦、吉他和快板撞上了橘子海,黄宏闭眼吹出了整个盛夏,赵本山贡献出了顶级鬼步,陈佩斯不仅让太空步有了京剧的版本,还在物理意义上诠释了什么叫平地起高楼。
在艺术家前辈们的铺排下,只听“咔嚓”一个炸雷,土生土长的二创实现了繁荣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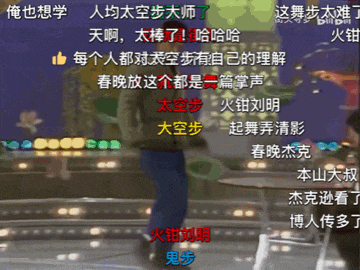
探戈,就是趟啊趟着走。
(图/小品《舞动春晚》)
02
押题,押出了蓬勃的
文化记忆
如此一来,谈论春晚,就几乎等同于在谈论某个大范围的文化现象。
早有博士论文开始抽丝剥茧地分析它,从审美到集体记忆,从“司马缸砸缸”到“现在相声明显干不过小品”,把它里里外外吃透了,甚至能打响春晚押题的第一枪。
在这轮春晚派生出的思想狂欢里,讲什么词、说什么事,攫取哪句爆梗,切磋哪种修辞,模仿哪个群体,全在二创博主们的胸臆里,哪怕全程只有“饺子”俩字,他们也有办法叙事,中国人常说味儿对了,摸不着、看不见,但观众们就是知道准确答案在哪儿。
经典再现,听懂掌声。
(图/《二进制小品》)
包括《春节组曲》,它开始走向极其广泛的语境里去,大提琴骤然响起,只要是民生话题,一概适配,从央视的“你幸福吗”,发散到金广发的“你相信健身教练吗”,街头采访不一而足,但这首诞生于1955年的曲子永恒。
连二次元都出来了。
(图/《一场很(没)有必要的春晚》)
“春晚”并不是一个偶然爆发的ip,反而,我们对它早已太过熟悉,从结构上分解它,从情感上咂摸它,于是才有了天马行空,甚至妙笔生花。
在它的全称中,有一个词叫“联欢会”:打破束缚地笑、坦诚明白地讲,这是集体进入幽默与共鸣的时刻。从1983年开始,观众也是联欢会的参与者,他们甚至有点播节目的权力。当年,马季拉着,指了指来电记录:“点播你的《阿q独白》太多了,不演说不过去。”这种临场的惊喜,就是自台下而起的。
说演就演,绝不含糊。
(图/《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》)
切换到今天,则是有话直说的二创们,以海量素材搭起了旁枝斜逸的集体文化记忆,他们熟读“公鸡中的战斗机”与“母猪的产后护理”,围绕春晚这件事娓娓道来,让曾经响过的包袱,抖出第二番效果来。
对于春晚,人们到底还是有执念,因为它穿过了一个集体的时间——零点。有点像爱因斯坦所谓的时间膨胀效应,它可延伸、可具有文化意义,甚至可停留,从1983年起,一直被讨论、模仿、研究到了2024年。
又逢春节,不再多说,祝读者们新的一年日子红火,锣鼓喧天,鞭炮齐鸣。
(图/小品《拜年》)

评论5